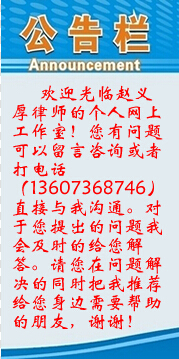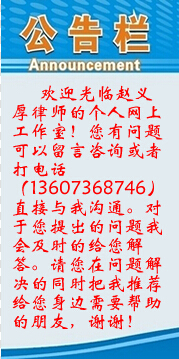文章详细
关键词: 空缺刑法规范/目的性限缩/创造性适用
内容提要: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创造,与法律发现一样,也是法官开展其司法工作的必要前提。构成要件规范事实与具体案件事实之间无法实现正常对接而使刑法规范呈现出的规范空缺,需要运用目的性限缩手段进行填补,以完成对空缺刑法规范的创造性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司法过程的首要行动就是法律发现。这里的法律是指针对个案的法律,即把法律发现聚焦在寻找正当的个案裁判依据,发现针对个案的解决方式,而不是由立法机关创立的体系性法律。由于成文法中不可能直接规定解决个案纠纷的详细法律,故成文法中也就没有与个案完全吻合的现成法律,共性的法律与个案结合,必须有法官等主动性、能动性的发挥,没有法官等的谨慎思维,反映事物共性的法律不可能与具有个性特点的案件自动结合。司法行动中的法官往往通过法律规范识别及法律规范解释,进行这一法律发现的过程。
其次,就是司法过程的法律创造问题。对司法过程的性质,卡多佐认为:“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发现法律,而是创造法律,所有的怀疑和担忧,希望和畏惧都是心灵努力的组成部分。在这里面,一些曾经为自己时代服务过的原则死亡了,而一些新的原则诞生了。”①但是,卡多佐所处的美国法治已经走过了形式主义法学的初级阶段,先例的拘束力原则以及对成文法的严格解释原则已经成为法官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我国,大部分法官还没有经过概念法学的严格训练,距离高水平的法官造法阶段还有相当的差距。另外,即使走过了法律形式主义的初级阶段,法官造法也是与人类关于法律的普适化方向相悖的,只要存在法治,就必然要求法律效力的普遍性。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创造性,这与法律发现一样,也是法官开展其司法工作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
(1)刑法规范是通过规定犯罪构成要件来对案件事实进行法律类型化的。构成要件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事实。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评价标准是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而不是具体的案件事实,即使是以前案例中曾经遭遇过的典型事实。已经对事实加以类型化了的构成要件与具体事实本身是内涵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过去发生的典型案件并不一定排斥今天发生的不典型的案件,而且即使是过去发生的典型案件,不过是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规范的目的和构成要件的特征,而未必是规范目的和构成要件的完整体现。因此,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关键还是看今天所发生的案件能否为已经对以前具体事实类型化了的构成要件所涵括。
(2)犯罪构成要件对案件事实进行类型化的过程中存在疏漏或漏洞是正常的。一般情况下,作为犯罪事实类型化了的构成要件,形式上未免是抽象的;再加上构成要件本身所蕴涵的规范的因素以及语言功能的限制,以及刑法的内在和谐与目的,使构成要件的内涵并不是一眼就可以透视的。必须通过解释来明确构成要件的规范性意义,并由此而使构成要件的抽象性、形式性向具体性、实体性靠近。②对于未被构成要件类型化的案件事实,则很难通过对其规范意义的正常解释,而使构成要件的抽象性、形式性向具体性、实体性靠近,构成要件的规范事实与具体发生的案件事实之间无法实现正常对接,亦即如果仅对构成要件的规范意义进行常规解释,无法“悟”出其应当涵摄的意义。这也就是漏洞概念的重要性:“只有当法律有‘漏洞’存在时,才承认法官有法的续造权限。”③
(3)构成要件的规范事实与具体发生的案件事实之间无法实现正常对接而使刑法规范呈现出的疏漏,一是与构成要件的要素缺失或过于限制有关。在构成要件理论上,构成要件要素是构成要件的下位概念和组成部分。各具体的构成要件都是由不同的要素组成。这些要素,在刑法理论上被称为构成要件要素。这些要素组成了犯罪构成要件的规范事实因素,如其在设定过程中出现要素疏漏或被过于限制,就会使具体发生的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的规范事实之间不能适应,而无法对接。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卡尔·拉伦茨所认为的“开放的漏洞”。④二是与刑法规范本身的不完整性有关。即对已经规定在刑法中的犯罪类型来说,欠缺对构成要件详细而无遗地记述,导致由于构成要件过于抽象难以确定其意义而使规范事实与具体的案件事实无法实现一一对应。⑤如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过失犯罪等。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卡尔·拉伦茨所认为的“隐藏的漏洞”。⑥
对于“开放的漏洞”,即法律应该规定某种类型而没有规定的,即作为一种“无意的沉默”,一般可通过类推适用的方法进行漏洞补充,诚如卡尔·拉伦茨所言,“填补开放的漏洞,通常是以类推适用,或回归法律所包含的原则之方式行之。……类推适用系指:将法律针对某构成要件(a)或多数彼此相类的构成要件而赋予之规则,转用于法律所未规定而与前述构成要件相类的构成要件(b)。转用的基础在于:二构成要件——在与法律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彼此相类,因此,二者应作相同的评价。易言之,系基于正义的要求——同类事物应作相同处理。”⑦
对于“隐藏的漏洞”,即“以法律规范意旨,原应就某类型消极地设其限制,而未设限制时,构成隐藏的漏洞。”⑧由于“漏洞存在于限制的欠缺”,⑨与其说是规范漏洞,倒不如说是规范空缺,与“开放的漏洞”这种“无意的沉默”相比,有“有意的沉默”之嫌,故笔者将“隐藏的漏洞”视为一种规范的有意空缺,并由此形成的规范视为空缺性刑法规范。填补“隐藏的漏洞”,“通常借‘目的论限缩’的方式创造出欠缺的限制规定,借此以填补此类漏洞”。⑩本文拟以不纯正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为视角,仅就如何通过目的性限缩(11)对空缺性刑法规范进行价值补充,从而实现对空缺性刑法规范的创造性适用。
二、空缺刑法规范之存在
大量存在的空缺刑法规范,与我国刑法犯罪构成要件的设定中存在开放的构成要件有关。(12)
刑法中的构成要件可分为封闭的与开放的两种。在封闭的构成要件情况下,构成要件具有违法性征表机能,行为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且无违法阻却事由即能认定其违法。此时,构成要件征表违法性,判定构成要件符合性的法官不需要再为判定行为违法而寻找其他条件,他只需要说明这不符合违法阻却事由即可。违反规范同违法性的这种毫无缺口的重合关系,即为封闭的构成要件(geschlossenen tatbestnden)。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由于立法者未能详尽地规定被禁止行为的各构成要素,构成要件并无违法征表机能,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但不能征表违法性。这样,仅确定无违法阻却事由,还不能认定行为的违法性,还需要法官积极查明是否存在着某些能够说明违法性的构成要件要素,以确定行为的违法性。这样的构成要件就是开放的构成要件(offene tatbestnde)(13)或称“被展开的构成要件”。(14)
德日刑法理论一般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过失犯,是典型的开放性构成要件。不纯正不作为犯中,不作为人应负的作为义务就属于立法者没能通过对构成要件要素的描述予以规定的部分,即使行为该当于构成要件,也不能表征违法性。由此,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情形下,法官必须对不作为人的作为义务积极查明,以帮助判断行为的违法性。过失犯也是如此。过失犯的违法性根据在于违反注意义务及发生构成要件所规定的结果这两个要素,而过失犯的注意义务在立法上是欠缺的,这决定了它同样属于开放的构成要件,需要法官适用时对这一欠缺部分予以补充。这种对于超出立法技术限度的那一部分,就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用“解释论”来补充法定构成要件。
开放的构成要件需要补充的部分,一般是违法性的价值判断要素。开放性的犯罪构成要件,作为一种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由于其不能通过其类型性为我们认识行为的违法性提供充分根据,在某些时候,还要求我们必须在构成要件要素之外寻找有助于违法性判断的要素;或者凭借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或者通过特殊的违法要素,或通过被遗漏的构成要件要素,来帮助判断行为违法性之有无,(15)这就要求法官必须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补充构成要件所欠缺的违法性要素,允许由法官对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补充,重新产生新的构成要件,以实现对诸如不纯正不作为犯及过失犯之类的犯罪的处罚。
由于我国与大陆法系刑法的犯罪论体系在实质内容上基本相同,这种情况在我国刑法中也就同样存在。(16)即我国刑法在犯罪构成的设定上也同样存在着构成要件规定的不完整性而由此导致的违法性判断上的非自足性,(17)使相应部分的刑法规范出现空缺,而进一步要求法官必须进行价值补充判断,这种空缺性刑法规范,导致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具体认定中呈现为:通过规定作为的犯罪类型事实“涵摄”不作为的犯罪类型事实,使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具体案件事实与犯罪类型规范事实之间无法实现正常对接。
以故意杀人罪为例,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实际上是有关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规定,这一规定是从规范的角度去涵摄通过所有作为的手段剥夺他人生命的案件事实。同时,这一规定还隐含着有关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如何从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中“解读”出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事实,如果仅从该罪所设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所规定的规范事实分析,也许能“解读”出发生了侵害他人生命法益的结果,但无法“解读”出行为人为什么会有为他人生命必须作为的义务、需要履行何种作为义务以及为什么不履行刑法规范并没有规定的义务就会构成刑事违法。由于“刑法对各种之罪多依作为而规定,至于与其相当之不作为犯则不设明文,而有待于审判者个别认定。”(18)因此,对于诸如故意杀人罪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认定,只能是通过相关刑法理论加以确定。这样,如何确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范围,即如何将作为义务与违法性连接起来,就成为一个在规范空缺且相当不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案例一:李家波故意杀人案(19)
1993年3月,刚满20岁的李家波和女青年项兰临相识并相恋,不久项兰临就怀孕,同年6月,李家波提出要跟项兰临分手并要项兰临去医院做流产手术,项兰临坚决不同意,几次欲跳楼自杀。同年9月5日中午,李家波回到宿舍,见项兰临在房里,就发生了争吵,项兰临喝下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瓶敌敌畏,此时,李家波非但没有及时救人,反而一走了之,临走时怕被人知道,还将房门关上。当天下午,项兰临被人发现送往医院,但因救治无效死亡。2000年4月9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李家波故意杀人案作出终审判决:李家波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案例二:王春全故意杀人案(20)
2000年4月25日,天津西青区王稳庄居民王春全与妻子王玉洁因家务事发生争吵,王玉洁气愤地跳进污水河中寻短见。王春全见状也跳进河中进行劝说,王玉洁不从,王春全随即独自回到岸上扬长而去,随后,王春全先到亲戚家中讲了王玉洁跳河的事,又给派出所打了电话。当公安民警和他的亲戚赶到河边时,时间已经过了近一个小时,王玉洁已经死去。2001年,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春全与王玉洁是夫妻关系,负有特定义务,王玉洁在河中,被告人王春全明知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却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放任结果发生,其行为已经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鉴于其犯罪后有自首情节,遂判处王春全有期徒刑6年。
案例三:吴某故意杀人案(21)
吴某在旅游风景区经营水上脚踏船出租旅游业务,1998年5月30日早上6时,吴某接待了6名游客,吴某的女儿将3条脚踏船租给了他们。7时许,因风太大,当地旅游部门通知吴某停止租船业务,8、9点钟的时候,吴某发现6名游客驶出了警戒线,便乘4人脚踏船追上他们进行警告,并与其中4人换船后独自回岸边,此时,风速加大,6名游客中的4人乘坐的大船被风吹到湖对岸脱险,但小船上的2人下落不明。岸上的人发现情况后找到吴某要求救助,但吴某没有采取任何营救措施,当晚,在湖东岸发现两名失踪者的尸体,一审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6年,赔偿两游客家属经济损失各33034元。吴某上诉,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吴某将船出租给游客后,就产生了在他们遇险时的救助义务,而吴某明知游客遇险,却没有履行义务,其行为是不作为的故意犯罪,原审法院判决不妥,应改判,因吴某积极赔付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各40000元,可从轻处罚。终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3年,宣告缓刑3年。
从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规定来看,其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所能涵摄的规范事实,与上述三案例中的案件事实之间显然存在巨大差异,无法实现正常对接,故在处理该三案件时,不能直接引用故意杀人罪的条款而不作任何加工加以适用。
对于案例一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行为人道德义务的不履行,就具有了刑法上的违法性?为什么当一对恋爱中的男女在家中,其中女方自杀或者由于其他原因生命危在旦夕,男方就具有道德上的救助义务,不救助就有可能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而如果此时邻居也看到了这位女方的处境,就可以说这个邻居有道德上的救助义务吗?实际上,她的男友和邻居都有道德上的救助义务,问题是为什么男友的不救助行为就可以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而邻居的行为则不构成刑法上的故意杀人罪呢?这说明,在具有道德上的救助义务的情况下,何种人道德上的义务可以成为刑法上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义务来源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范围。另外,如果一对恋人,男方在女方遭遇他人强奸的时候,自己却没有履行救助义务,也没有向相关机关报案,是否构成强奸罪呢?结论显然是否定的。但为什么强奸罪不能由不作为构成,而故意杀人罪可以由不作为构成?从刑法规范的角度出发,是可以肯定强奸罪的不作为犯的。但问题在于,在何种程度上肯定强奸罪的不作为的救助义务?恋爱中的男方对于被害人的生命有救助的义务,如果没有实施救助而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成立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同样,在其女友遭受强奸的情况下,也具有道德上的救助义务,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不能转化成法律上的救助义务,也就是说,同样的道德上的救助义务,在具体犯罪的认定上转化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这说明何种性质的义务,在何种情况下能够成为刑法上的义务来源,实际上也没有确定的范围。
对于案例二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王春全对其妻的自杀行为是否存在防止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如果有这种作为义务,那么其根据是什么?为什么不履行这种作为义务具有了刑法上的违法性?婚姻法明文规定的夫妻间的相互扶养义务是否当然包括相互救助义务?如果包括,这种法律义务是否必须经过刑法认可?从我国现行刑事法律看,没有关于夫妻之间具有相互救助义务的明文规定,如果把对“婚姻法对夫妻之间扶养义务的规定”理解为当然包括夫妻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法律救助义务,那么,因为没有得到刑法规范的确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仅有“婚姻法对夫妻之间扶养义务的规定”,这是否可以成为被告人不负刑法意义上的救助义务的抗辩理由?
对于案例三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尽管基于合同可以引起合同法上的义务,但合同法上的义务如何转化为刑法意义上的义务?合同法上的义务能否成为刑法上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义务来源?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刑法上的故意杀人罪的义务的来源?这恰恰都是刑法没有规定的。
三、目的性限缩与规范空缺之填补
诚如拉伦茨所言,填补隐藏的漏洞,需“添加——合于意义要求的——限制。借此,因字义过宽而适用范围过大的法定规则,其将被限制于仅适用于——依法律规整目的或其意义脉络——宜于适用的范围,质言之,其适用范围即被‘限缩’。”(22)这种“目的论限缩的正当理由,即在于下述正义的命令:不同类的事物应作不同的处理,质言之,应依评价作必要的区分。”(23)
那么,如何运用目的性限缩填补刑法相关规范空缺,以完成对空缺刑法规范的创造性适用?
不纯正不作为犯刑法规范空缺填补的核心问题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刑事违法性及可罚性问题。
在规范视野里,刑法中规定的犯罪只有纯正不作为犯和作为犯两种。不纯正不作为犯正是以不作为形式构成的“作为犯”,本质上,它是“作为犯”的一种事实状态。换言之,不纯正不作为犯符合的并不是自身的构成要件,而是作为犯的构成要件。不作为与作为的事实结构不同,不作为以违反作为义务为基本内容。由于刑法中没有对作为义务的种类和范围做出规定,加之对同一义务的违反往往随案情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危害后果,这就必然造成不纯正不作为犯内涵模糊,外延宽泛,界限不清。因此,要以作为犯的构成要件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就必须解决两者的等置问题,即以不作为方式构成的犯罪事实与通过作为方式构成的犯罪事实在违法价值上相等。(24)而这一问题解决的前提条件,是如何确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范围,即作为义务来源的确定。
由于“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情形中,把不作为人的所有情况都比较详细具体地规定在构成要件中是不可能的。关于这部分内容以没有规定的构成要件来加以补充,这并不是由于解释上的困难才这样做,而是由事物本身性质决定的。”(25)这使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在对不纯正不作为犯进行处罚时,必然要由法官将未规定在条文之中的作为义务予以补充,经过补充之后,不作为人不作为行为的违法性才能最后确定。法官对最终的作为义务的确定,则往往是由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形决定的,也就是说,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往往是具体案件事实中的作为义务。
这种作为义务,目前就刑法理论的通说而言,主要有四种:
首先,关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
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是不纯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但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是否仅限于刑法中的义务?通说认为,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不仅限于刑法明文规定的义务,还包括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关键是违反民法、行政法等法律明文规定义务的行为,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刑法上的义务来源。
其次,关于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
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其职务和业务要求他负有某种积极作为的义务。由于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所涉及的往往是相关行政法规范所规定的义务,这种行政法规范上的义务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刑法上的义务来源,特别是成为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来源,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例如,根据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医生具有救死扶伤的义务。问题在于,这种义务能否成为刑法规定的义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刑法规定的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义务的来源。如果在一个病人生命危急的情况下,被送往医院,但由于无钱治疗,交不起住院费而医生不予救助的话,医生是否构成刑法上的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也就是说医生的义务来源是否要求以病人的付费为前提,即是否要求成立合同关系为前提。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医生具有救助病人的义务,但如何确定医生的救助义务何时、在何种情况下成为刑法中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作为义务,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难做出判断的问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再次,关于契约或法律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
契约或法律行为往往具体设立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因此可以产生作为义务。如果因不履行该义务而给刑法上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严重损害的,可能成立不作为犯罪,如受雇保姆有照顾婴儿的义务。不容否认,基于合同当然可以引起合同法上的义务,但合同法上的义务能否转化成刑法上的作为义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成刑法上的故意杀人罪的义务的来源,并不能一概而论。
最后,关于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
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是指因自己的行为导致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危险而产生的采取积极行动防止危害结果现实发生的义务。实践中先行行为的范围如何界定?是否所有的先行行为都可以导致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作为义务?即如何认定先行行为在何种情形下能够导致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义务,也是一个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问题。
另外,还有道德上的义务。
我国刑法理论上对道德上的义务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在实践中,一般都认为恋爱中的恋人、同居的男女等,彼此在道德上互相负有救助的义务,如果一方在他人遭遇生命危险的时候,可以实施救助行为而不去救助,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一般认为是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关键问题在于,道德上的义务较之前述法律上的义务,其更不具有明确性,因此,如何确定行为人的道德义务可以成为法律上的义务便成为难题。
由此可见,由于不纯正的不作为犯,其义务来源刑法并没有作明确规定,因此,除上述列举的义务来源之外,还可能存在其它的义务来源,如按照某些传统习惯应当承担的特定作为义务等。在特殊场合下,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也是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因为审判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着对于不防止前恋人自杀的男子的不作为以故意杀人罪论处的判例。(26)但问题在于,上述义务是否都可以转化成刑法上的义务,或者说任何人的上述义务是否都可以转化成刑法上的义务呢?因此,在弄清楚了不作为的义务来源范围的基础之上,有必要在这些义务中具体确定谁的义务能够成为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义务来源,或者说这些作为义务是否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这就需要解释为什么上述诸多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的义务,也可以转化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作为义务,为什么“他的”不作为能够构成犯罪,而其他人的却不会呢?这一刑法规范空缺的填补,是法官通过作为犯与不作为犯两者在价值上的等置,即合理限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使它能与作为犯在法律上等而视之,即以不作为方式构成的犯罪事实与通过作为方式构成的犯罪事实在违法价值上相等,进而确定不作为犯在价值上的违法性才得以完成的。(27)
而不纯正不作为犯要与作为犯在法律上等置,应当具备两方面条件:(1)不作为事实结构要素齐备;(2)不作为与作为犯罪价值上的相等。前者为事实判断,后者为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是一种形式的判断,为价值判断提供物质对象;价值判断则具有实质的内容,最终决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可罚性。等价性判断把一些不符合实质条件的不作为事件排除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之外,从而起到限制处罚范围,维护罪刑法定的作用。等价性是一切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必须具备的内在品性,只有通过等价性,才能实质地限制作为义务成立范围的办法,求得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的等价。(28)
法官应如何进行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的等价判断呢?亦即如何将上述的所谓道德的义务、法律的义务等转化成刑法上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义务,并且在认定这些义务可以转化为刑法上的作为义务后,又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义务的能力呢?确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价性,固然离不开对作为义务范围的合理圈定,但是必须明确,确定作为义务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解决等价性问题的一个环节,只有找到不纯正不作为犯和作为犯等价的媒介,才能最终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问题。由于“不作为的等价性是一个综合评价的要素,须以各种犯罪所包含的危害性质和违法特征为判断基础,而就特定情况下的不作为与通常实现该种犯罪的作为相比较,以判断该不作为是否与作为的价值相当。”(29)因此,法官在对具体案件如何进行具体的等价评判时,一般应考虑以下几类因素:
(1)社会的道德水准。当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较高时,我们可以将刑法之外的其它法律上的救助义务和道德上的救助义务乃至其它的义务在更大的程度上转化为刑法上的义务。但一个社会环境中道德水准普遍偏低时,刑法之外的其它法律上的救助义务和道德上的救助义务转化为刑法上的义务的程度就低,因为在这种道德水准较低的情形下,不履行救助义务的人占多数,如果将所有的人都定故意杀人罪,显然是不符合人们的感情的,也有悖法秩序。从这一角度也说明了道德对法律适用的影响。
(2)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如医院的“见死不救”。目前实践中对于医院的这种“见死不救”的做法并没有处以法律上的责任,更不用说对具体负责的医生科以刑法上的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这是因为,在医院自身的生存都需要靠赚取医药费维持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病危的病人被放在医院门口,在其没有交纳费用的情况下医院都有义务去救助的话,医院的救助义务太宽了,如果医院切实履行这种救助义务的话,医院的生存都会成为问题,最终救死扶伤义务也无法履行。
(3)救助方的救助能力。如上所述,共同生活的恋人、夫妻,都有救助的义务,至少是道德上的救助义务。但法不能强人所难,如果救助方的救助能力有限的话,则不能强求。亦即义务人“必须具有个人作为能力,而对防止构成要件该当结果之发生,具有事实可能性者,其不作为始具不法品质,而有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之可能。”(30)
(4)救助人与被救助人的关系。救助人与被救助人关系的不同也决定了救助人的救助义务能否转化成刑法上的故意杀人罪的义务来源,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刑法上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义务来源。如果救助人与被救助人关系密切,诸如夫妻、恋人、或者说是很好的朋友,或者说受害人对施救人的依赖程度较高的,那么其救助的义务转化为刑法中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作为义务的程度就高。
(5)救助义务不仅仅是有无的问题,还涉及程度的问题。作为义务的强弱与不作为所构成之罪的轻重,应是成正比的。过路人发现火灾不救火的行为,之所以不构成犯罪,实质上是因为其作为义务弱因而导致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轻;消防队员发现火灾不救火的行为,之所以构成犯罪,实际上是因为其作为义务强因而导致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重。(31)不同人的不作为,由于其作为义务的强弱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
(6)作为义务紧迫性的问题。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当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刑法对此种行为规定了遗弃罪,但问题在于,如果这种抚养的义务具有紧迫性时,行为人没有去履行抚养义务的话,则可能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即这种抚养义务就可能转化为刑法上的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义务来源。
(7)考虑不作为人的主观方面。即通过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情况来判定不作为和作为是否等价。这种观点主要见于日本的判例,如认为成立不作为的放火罪,仅有相当于放火罪的故意的认识还不够,还必须具有“积极利用已经发生的火灾”的目的。(32)
(8)被害人被救助成功的可能性。当受害人生命处于垂危之际,义务人即使实施救助行为,也没有可能或者说可能性极小的救助其生命的情况下,行为人没有实施救助行为也不能认为是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9)以社会的一般观念来评价作为的可能性。即使作为义务可以转化为刑法上的义务,但如果行为人不具有作为的可能性的话,也不能认定为是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正如日本学者大谷实所指出的:“作为的可能性,是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作为义务的基础,因此,必须以一般人或社会的一般观念为基准进行判断。”(33)
(10)基于犯罪性质的不同,应对不纯正不作为犯进行具体判断。基于犯罪性质的不同,对于不作为犯罪的认定也就不同,例如,丈夫见妻子被他人抢劫、抢夺、盗窃而不实施救助,很可能不构成犯罪,但若见有人要杀害其妻子而不实施救助,就有可能要定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当然,也可能考虑定遗弃罪。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进行规范填补时,除考虑上述因素有无外,还涉及程度问题。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这些判断还会发生变化。“不作为犯罪的义务不仅是一种作为义务,而且是一种特定的义务,并且是基于某种特定的条件而产生,随着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的”。(34)在我国,随着社会成员协作的加强,社会形态每时每刻无不在变化之中,不作为犯罪特定义务的范围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会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但毕竟,由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构成要件属开放性的构成要件,在具体认定时不像作为犯或纯正不作为犯那么明确,过度扩张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认定不利于保障人权,与我国现有的刑事政策也是相违背的。因此,法官在实践中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进行规范补充时,对于行为人的作为义务的认定采取的是一种限缩而不是扩张的态度,就成为一种必然的价值选择。
注释:
①[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5页。
②参见[日]小野清一郎著:《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③[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7页。
④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4页。
⑤参见刘艳红:《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2-153页。
⑥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4页。
⑦[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8页。
⑧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⑨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4页。
⑩[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5页。
(11)“目的性限缩系指对法律文义所涵盖的某一类型,由于立法者之疏忽,未将之排附在外,为贯彻规范意旨,乃将统一类型排除在法律适用范围之外漏洞补充方法而言。”参见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12)参见刘艳红著:《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158页。
(13)参见刘艳红:“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之提倡”,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
(14)参见[日]福田平、大塿仁著:《日本刑法总论讲义》,李乔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15)参见刘艳红:“论大陆法系违法性判断理论的缺陷及弥补”,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
(16)参见刘艳红著:《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17)参见刘艳红著:《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156页。
(18)韩忠谟著:《刑法原理》,台湾1981年作者自版,第101页。
(19)邵红英、大立:“未婚同居,见死不救,不作为也是故意杀人”,载《检察日报》2000年5月24日,第7版。
(20)刘荣庆、陈彦、孙水根:“吵架了,就可以不管妻子了吗?”,载《检察日报》2002年4月30日,第7版。
(21)王刚、韩云鹏:“船主见死不救被判故意杀人”,载《哈尔滨日报》2002年5月11日,第6版。
(22)[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7页。
(23)[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8页。
(24)参见刘士心:“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价性问题”,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
(25)[日]日高义博著:《不作为犯的理论》,王树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26)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
(27)参见刘士心:“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价性问题”,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1页。
(28)参见刘士心:“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价性问题”,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1页。
(29)洪福增著:《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218页。
(30)林山田著:《刑法通论》,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304页。
(31)参见张明楷:“论不作为的杀人罪”,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2)参见黎宏著:《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113页。
(33)[日]大谷实著:《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34)陈兴良:“论不作为犯罪之作为义务”,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