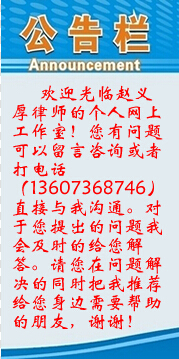证明标准问题应当分为两个层面进行考察:作为立法问题,证明标准问题针对的是裁判尺度,其关键在于有罪裁判的尺度的立法选择与表述;作为司法问题,证明标准问题针对的是裁判事实,即如何推动更多的案件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以及如何保证裁判者宣称已达证明标准的案件确实达到了证明标准。证明标准与裁判事实的关系犹如丈量土地的标尺与依据该标尺丈量后的土地。尽管标尺的选择直接决定着丈量的结果,但是,二者却很大程度上是彼此独立的问题。
区分这两各层面的问题对于刑事证明标准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国证据学理论中,曾一度忽视证明标准的司法兑现问题,忽视对保证证明标准如期兑现的制度、机制的研究,由此造成了:尽管“客观真实”的诉讼理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在司法实践中,保障裁判客观性的制度(如证据裁判原则、直接言词原则、证人出庭)却长期未能真正建立。然而,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无法自行兑现。缺乏了制度的依托,尽管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善良且美好的理想状态,犹如未考察地基和砖瓦的质量而建立的高楼一样,建立在证人不出庭、裁判者不直接接触原始证据等基础上的司法实践根本无法兑现客观真实的理想。
在近来的证明标准讨论中,对上述两个层面问题的混淆则导致了一些无谓的争论。围绕裁判事实能否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而展开的争论即是典型的一例。有学者认为,裁判事实不可能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并据此对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提出置疑;而捍卫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的学者则据理力争,并以活生生的事例证明,裁判事实当然能够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够如此。显然,在司法实践中,裁判事实达到客观真实程度的案件不乏其例。某人被判杀人罪,而事实上他确实杀了人;某人被判盗窃,而事实上确实实施了盗窃……公众诸如此类的社会经验恰恰是支撑刑事裁判制度正当性的重要支柱。因此,从裁判事实入手否认刑事裁判能够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不可能令人满意。然而,承认上述事实却依然无法回答如下疑问:部分案件能够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能否作为“应当以客观真实为证明标准”的论据呢?换句话说,以客观真实为证明标准是否科学与(部分)案件的裁判事实能否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是彼此分离的两个问题,以后者否定或支持前者都无法让对方心悦诚服。因此,理论界关于裁判事实能否达到客观真实程度的研究与论争,对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的存废问题并不具有直接意义。
在区分证明标准与裁判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的缺陷不在于只有部分案件可以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其实,无论我们采用什么证明标准,都只可能是部分案件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而在于,裁判者在裁判当时根本无法知晓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客观真实的程度。作为知情人或者旁观者,我们当然可以说,裁判者在裁判被告人杀人罪时,他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正确反映了客观事实。然而,就裁判者而言,在根据证明标准进行裁判的当时,他如何能够知道自己的认识是否已经达到了客观真实的程度呢?如果我们脑袋里没有预先知道拿破仑死亡的日期,当别人说“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时,无论我们认为该判断是真还是假,我们都无法对我们自已的判断是否合乎客观事实作出裁判。当然,在哲学上,正确反映客观事实的认识是一种终极性判断,具有不依赖于个人意志的绝对性和超越时空的有效性。如,作为一个反映客观事实的认识,“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的判断自1821年5月5日以后即具有了绝对的效力。达到客观真实程度的裁判事实也是如此。对于一项达到客观真实的裁判事实,无论裁判者是否清醒地知道这一点,它都将具有超越时空的有效性。因此,他人(如知情的当事人、证人)当然可以对裁判者的认识进行是否符合客观真实的判断。尽管裁判者在裁判当时无法对自己“有关案件事实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真实作出判断。总之,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的缺陷不在于认识的结果方面,而在于判断的方法方面。由于裁判者无法对自己的认识是否达到了客观真实的程度作出判断,以客观真实作为裁判者有罪的裁判尺度不适当且不具科学性。
在当前诉讼法学界,对于放弃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如此以来,等于降低了证明标准的要求,而降低证明标准将导致冤假错案的增生。对此,应当辨明两点:
首先,应当承认,“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确实低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在认定有罪问题上,主观认识符合客观事实是我们理应追求的目标。但是,任何法律必须对完美的正义要求作出现实的妥协。而且,从证明标准的设置上看,证明标准应当以正当性的最低限度为标准而不是以所要追求的最高理想为尺度。由于方法论上的原因,我们无法要求裁判者以客观真实作为裁判的标准,只能退而求其次,设置一种以“最大限度贴近客观事实”为要求的衡量尺度;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尽管并不能担保认识结论的必然正确,却要求必须得到一个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错误可能的结论。
其次,以低于客观真实的“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标准并不必然导致定罪实际质量的下降。证明标准只是一种最低的正当性要求(如,60分才能及格);基于此种标准裁剪出的认识结果尽管必然不得低于特定的限度(及格者必然不得低于60分),却可以远远高于最低标准(及格者有可能是100分)。因此,在实质意义上决定裁判事实质量的不是证明标准,而是该裁判事实所立足的证据以及产生该裁判事实的诉讼过程。更重要的是,对此问题的考察,必须置于我国诉讼制度的特殊构造之下才可能得出全面地认识证明标准与裁判事实质量的实际关系。在我国,讼制度的构建是以客观真实为指向的,但是,此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实现的。就证明活动而言,第一审有罪判决实质上包含着起诉方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因此,一审裁判有罪后,如果对自己是否实施刑法禁止行为最为清楚的被告人提起上诉,第二审法院将依据同样的证明标准对案件事实重新进行考量;如果第二审法院亦坚持有罪的看法,此时,尽管其裁判的证明标准与第一审裁判相同,在裁判事实的实际质量上却已经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累加效应,此种累加后的认识必将超出同一证明标准在起诉时或第一审裁判时的实际质量。此种认识累积效应的道理很简单:吃一个烧饼远远不能添饱我们的肚子,但是,如果连续吃上五个烧饼却可以让我们吃得很饱。因为后一个烧饼在之前烧饼的基础上将产生单个烧饼不可能产生的巨大作用。死刑复核程序亦是如此。在论证为什么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死刑复核程序时,多数学者认为,“减少一道程序,就意味着增加了一些事物的可能性;增加一道程序,就增加了一些可靠性”,其中所蕴含的亦是上述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