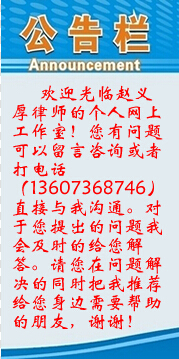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的确立对保障人权、维护法制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由于司法实践中某些审判员对该原则的机械理解,导致对若干案件不能正确地予以处理,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本文试就其中比较典型的两种情形予以剖析,以求有助于司法实践。
一,从形式上看,刑法分则条文对某一行为有具体明确规定,就想当然地认为该行为一定构成犯罪。
一般而言,只要刑法分则有明确规定,就应该认定该行为构成犯罪。但在具体处理案件时,切记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能只看形式,不看本质,即罪刑法定要求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符合法律规定,更要求实质上违反刑法规范。在这方面,司法解释即最高司法机关对法律的理解,可以为证。如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245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滥用职权,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的,就要以非法搜查罪或者非法侵入住宅罪,从重处罚,而没有其他任何情节上的限制。这样,从形式上看。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只要实施了上述行为,就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但是,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搜查,只有在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手段恶劣;引起被搜查人精神失常、自杀或者造成财产严重损坏的;明知是与涉嫌犯罪无关的人身、场所非法搜查的;3次以上或者对3人(户)以上进行非法搜查的,才能予以立案。也就是说,司法机关认为,有些行为形式上尽管符合某个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并不一定就构成犯罪,还必须是该种危害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成立犯罪。这种司法解释在其他的许多犯罪中都可以见到。当然,司法解释不能对每个罪都予以具体化,既使细化的司法解释本身也存在需要进一步理解的问题。因此,在定罪实践中,应切实注意做到两点。
一是定罪时既要考虑目,即刑法分则具体条文,又要考虑纲,即刑法总则规定,更要把握总纲,即刑法总则第十三条关于社会危害性的规定。
例如,被告人索某从市场上购买一支发令枪,经过改装,成为一支火药放射枪,经司法技术鉴定,该枪在近距离内(二米)射击可以致人轻伤。对此行为,某区检察机关以非法制造枪支罪提起公诉,某区法院以同样罪名予以定罪量刑。
此案从表面看,被告人索某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25条关于非法制造枪支罪犯罪构成的形式要件,而且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只要非法制造一支以上火药发射枪就可定罪的司法解释看,也够立案的条件,即司法机关的定性是准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立法原则,就会发现该定性存在的问题。非法制造枪支罪是一种重罪,立法机关将其放在危害公共安全一章里加以规定。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枪支的潜在危害比较大,一经使用,即可能给人的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但具体到本案呢,被告人非法制造的枪支面对面地近距离射击,才能致人轻伤,其威力甚至连一把匕首、一根铁棍也不如,其对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对他人的生命威胁显然不大,因此,从社会危害性角度考察应属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以犯罪论处的范畴。
再如,有观点认为,对数额犯,只要行为人达到刑法条文或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标准,就不存在不构成犯罪问题。这也是对罪刑法定的片面理解。比如盗窃,如果行为人盗窃达到数额较大,例如800元,就符合了犯罪条件,属于盗窃犯罪。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犯罪动机、犯罪后果以及其它一些较轻情节要考虑,也还存在从整体评价上看,尚有存在情节显著轻微的可能。即刑法第13条前半段所言属于构成犯罪情况,而但书是指这种行为按前段规定是犯罪,但立法者法外开恩,认为此行为情节显著轻微而不按罪论处。事实上,不要说数额犯,即象杀人、放火、强奸也还存在情节显著轻微不以犯罪论处的情形。
二是即使对刑法分则具体条文本身,也要考虑其上下文意思、上下款的内在联系,而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孤立地看待。
例如就无限防卫制度而言,有观点撇开刑法第20条第一、二款不论,而仅就第三款的字面意思来理解。该观点认为,在刑法第20条第3款限定的犯罪范围内,公民行使正当防卫权、反击不法侵害人时所采取手段的强度没有限制,其中包括任何足以致不法侵害人于死地的手段。按照该观点,只要是针对该类不法侵害实施的正当防卫,即使该不法侵害的程度轻微,亦可对之采取致其于死地的防卫措施。
事实上,作为正当防卫特殊形式的特殊防卫行为,尽管有其特殊性,但还必须在正当防卫一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否则就不属正当防卫的范畴,即该款实际是对本条一、二款的补充,或者说是对其中特殊情况的进一步强调、明确。其立法宗旨在于使第二款规定更具有透明度和操作性,以便于实际操作部门在处理特殊防卫案件时,更准确地把握第二款所规定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真谛所在,尤其是不能受不法侵害者伤亡这一损害结果的影响。也就是说,该款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一、二款原则规定的指导下发挥其特殊性的。他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补充和被补充、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对此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防卫行为,不能不分轻重,一律采取致侵害人于死地的方式,即在此类场合下,仍有防卫过当存在之余地。
二、从形式上看,刑法分则条文对某一具体行为方式没有具体明确规定,就想当然地认为该行为一定不构成犯罪。
法律条文是抽象的、概括的,任何一部法律都只能描述事物的本质属性,不可能穷尽所有具体的事实情境并给种种情境以十分确定的法律后果。因此,实行罪行法定,绝不是宣告法律已经现成,法官只须对号入座即可。但现实情况却是,有些司法人员对罪刑法定的理解,就是限于法律规定的字面意思,认为按法律规定的字面含义不能包括的行为就不能定罪。在这种观点看来,渔塘边立一块“严禁垂钓,违者治罪”的牌子,如果行为人垂钓,那就构成犯罪;如果撒网捕捞,则因没有明确禁止,就不构成犯罪。
例如我国刑法第262条规定了拐骗儿童罪。拐骗儿童罪是收养为目的,将儿童骗走,其行为方式是“骗”。据此,有人认为以收养为目的盗窃婴儿就不能按此罪论处,因为此种行为的行为方式是“偷盗”,而不是“拐骗”,对象是“婴儿”而不是儿童。
事实上,上述案例的错误是明显的,按照法理,法律把低度的危害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高度的行为,既使法律没有涉及,也当然包括在犯罪范围之内。既然拐骗儿童构成犯罪,而拐骗是以犯罪对象具有一定的思想意志为前提,那么偷盗一个没有思想意志的儿童,危害更为严重,更要构成犯罪,这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应该说属于法理上的当然解释。事实上,这个原则早在我国唐律中就加以规定,即“举轻以明重”。再如如果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并且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构成偷税罪的轻罪;如果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构成偷税罪的重罪。但是,对于纳税人所偷税数额达到应纳税额的30%以上且在1万元以上但不足10万元的,以及偷税数额占应纳税数额的10%以上不满30%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情况,有人认为不能按罪论处,其理由是刑法没有对这种行为予以明确。再如父亲把亲生儿子卖掉,有人也认为因缺乏“拐”这个要件而不构成拐卖儿童罪等等。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追求形式意义上的罪刑法定,而忽视了实质意义上的罪刑法定。
为了克服这种错误,这就需要法官从立法者原意出发,领悟刑法精神,需要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准确地适用刑法。要明确法官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根据条文简单地对号入座,机械地适用法律,而是案件能动的裁置者,是能够将法律条文与案情、与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等等灵活结合的法律精英。
其一,法官要成为探索法律真谛的人。法律同其他事物一样,有其形式,有其本质,法官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努力探求真谛。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文明成果在法制领域的体现需要我们学习、研究;古今中外定案的根据、原则,需要我们批判地继承、合理地“扬弃”。例如天理、国法、人情是我国古代定罪要考虑的因素,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经验结晶,就需要我们在定罪时予以借鉴。即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定罪量刑不但要考虑国法,还要考虑天理、人情。所谓天理,是指自然的法则、自然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当属此类;所谓人情,在唐代以前称之为民情,后来为避李世民的讳才改为人情,是指民众的普遍感情、观念,它是一种在文化传统、民族风情潜移默化下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实际上,现代法制社会也把民情作为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方式予以考虑,例如美国在刑事审判中,定罪的主体不是精通法律的法官,而是法律知识相对欠缺的陪审团成员,这即是从普通群众的观念上、从民情上考虑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我们在定罪时,多考虑一些民情,也许就会少办一些错案。例如,15岁的李某把邻居的一幼童骗到河滩上杀死,而后向其家属索要钱财。对此绑架案,有些办案人员认为不应定罪,其理由是,刑法对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应负刑事责任的案件作了具体规定,即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其中不包括绑架罪。但一般老百姓却认为,这种行为不定罪实无天理。老百姓的这种说法,应该说是民情的一种体现。实事上,后来的立法解释也为这种“民情”的评价给予了肯定。
其次,法官要做深刻领悟现实生活中的人。刑法虽然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罪刑法定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绝对值,罪的范围和刑的幅度总是存在一个模糊的界域,即使最易适用法律条文的故意杀人罪,也因存在何为“杀人”而有所争议,例如对安乐死、对某些见死不救行为等等就存在诸多争议。也就是说,任何案件都无法照搬照抄,因而对国家社会发展大局的把握对于法官正确办案是必不可少的。法制社会要求法官深刻领悟社会现实,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国家都规定有初任法官的年龄限制,例如加拿大规定45岁以上的人才能初任法官,其目的就在于让法官领悟社会现实更为深刻一些。
总之,作为一名刑事审判法官,要正确定罪量刑,就决不能象社会上的一些人,甚至个别法官认为的那样,简单地套用法条,仅从法条的字面意义上理解,片面地追求形式意义上的罪刑法定,而应当努力探求法律真谛,深刻领悟社会现实,结合社会现实不断创新。当然,这种创新不是类推,更不是发明创造法律,而是把法制的精髓与当代社会现实相结合,赋予其合情合理的含义,达到灵活准确适用法律的目的,以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