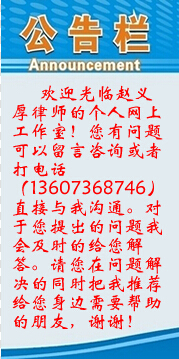比较法经验表明,司法判例并不是被制定的,而是逐步“形成”的,是法律共同体按照逐渐形成的同质化的思维惯性或技术模型而形成的裁判理路;判例的权威或效力也不是被赋予或强加的,而是被“遵从”的,是那些已成为法律人共识的裁判理路在具体案件中被具体法官自觉地或惯性地服从。这样的理路、这样的同质、这样的思维惯性和相应的服从自觉,需要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长期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被制度赋予某种“指导”效力的司法判例与案例选编的总体目标和功能价值并无二致;只是指导性判例以其关注度更高、聚焦点更集中、受众面更大等优势,可能推动同质化过程的更快发展,因为每一个指导性判例的形成和适用过程本身就浓缩了众多法律人共同探寻裁判理路的同质化过程。
进而言之,在我国讨论判例制度——又称案例指导制度、先例制度、先例判决制度、示范性案例制度等等,均指以成文法为背景,在个案中以特定事实为基础作出的终局裁判,在同一司法区域内对相同或相似的其他案件发生说服效力(而非拘束效力)的制度。当然,名称并不特别重要,因为除非已有确定的内涵,概念本身只是一个符号,重要的是这个符号的内涵和外延必须界定。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判例法”,因为“法”本身已明确具有“拘束力”的内涵,而这是在比较法文献中明确界定为普通法系所特有的判例制度。尽管某些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最高法院的判例说服效力已接近于拘束力,但在法律意义上仍不能视同于普通法系国家的判例法。不过另一方面,我国判例既然作为一种“制度”,其对后案的效力虽仅止于“说服”,却不能仅限于后案法官基于个人认同或偏好而自愿受前案判决的影响,至少,在被识别为“同类案件”的前提下,与前案判决明显冲突的后案判决可能受到某种权威的干预,比如成为上诉法院改判的理由,或者在德国上诉程序中成为获得特别上诉许可的事由、在我国应成为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或提起再审的事由。
然而,在两大法系的趋同化发展已在许多领域中严重模糊了传统分界的当代,判例制度与其说是传统或观念问题,不如说是技术问题。这一技术依赖于若干制度的支撑,因而借助判例制度探寻审判理路,必然带来相应支撑性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比如,判例首先意味着一案的判决效力及于本案以后的其他“同类”案件,因此“识别”一案(后案)与作为判例的案件之间的类似性,就成为适用判例的基本前提,而这一功能是由裁判文书直接承载的。具体而言,识别案件的依据是裁判理由部分的“事实”,那么,法官的事实认定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之间、法律事实与法律要件及法律规范适用之间、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与回应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裁判结果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目前司法实践中普遍发生“证据→事实(+法律评价)→法律事实→法律要件满足→适用法律→支持诉讼请求”这一逻辑链条断裂的现象,甚至由证据认定直接跳转到支持或否定诉讼请求的裁判结论。这些错误一部分归咎于我国现行裁判文书在结构上即未按照裁判的理路进行设计和要求,比如,裁判主文与裁判理由之间有相对划分、裁判理由与事实构成之间并无真正区分,如果不进行修改,这样的裁判文书很难承担起判例制度所必须具备的案件识别功能。
毋庸赘言,判例制度在统一司法和通过统一、一致地解释法律从而渐进地发展法律方面的功能或价值已广为认识。在中国这样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却实行单一制政体的大国,特别是在政策形成周期短、规范化和确定性程度较低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纠纷急剧增长与司法资源严重短缺的冲突之中,司法判例的上述功能更加凸显。此外,示范性个案判决为批量生产司法产品提供了模板,从而在整体上促进高效率司法;通过渐进地发展法律而节省立法成本和减少法律秩序振荡。但判例的权威性,除了如前所述的法律职业同质化过程之外,作为制度性指导,则主要取决于创制判例的主体和程序的权威性。就其本质而言,判例制度意即一案的裁判 “在本辖区内”对其他相同或类似的案件(下简称后案)产生说服效力。一个基层法院的判例对本院的后案、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的判例对本院及其所辖各下级法院的后案、最高法院的判例对于本院及最高法院的辖区即全国法院的后案发生说服效力。因此,由最高法院垄断司法解释权和判例形成权的做法并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判例制度;判例制度的基本原理是,个案裁判的效力范围与裁判主体的权威性和裁判程序的庄重性大致相当。
具体而言,如果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在结构上完成专业化改造、在权限上定位于法律事项,那么审判委员会作为本院判例主体、以维护同类案件在本院内司法统一,正是实行分项管辖模式的成文法国家在最高法院层面上以形式相似的联合审判庭(德国)或法官大会(法国)所承担的功能。不过,其前提是改变审判委员会听取汇报的决定模式,而必须像法律审程序的法官一样阅读卷宗,并在必要时开庭听取各方律师的陈词和辩论。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审判过程,审判委员会也因此有权并有义务作为大合议庭的法官在裁判文书上署名,成为真正意义的裁判者。
各上级法院以上述方式形成的审判委员会裁判对于本院和辖区内下级法院的同类案件应具有制度性说服效力。但需要强调的是,上级法院推翻下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形成的判例时,需要以同样权威的审判委员会构成和决定程序。如果上级法院仅以审级的优势,以一个年龄、资历、审判经验、专业水平等任何方面的权威性都处于下风的合议庭(甚至实际上只是承办法官一人),推翻下级法院由资深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依据审判程序作出的裁判,这样的上级裁判不仅作为整个辖区下级法院的判例难以具有权威效力;而且即使是针对本案,也只能是基于法定审级而具有法定效力,而无法基于审判权威而真正产生判例意义上的说服效力。
司法裁判作为判例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裁判主体的权威性、裁判对象的普适性和裁判效力的终局性。判例制度意味着一案的裁判对“本案以外”的其他类似案件产生一定效力,是个案裁判对本案效力的向外延伸。因而,离开裁判的终局性,无从讨论判例或案例的效力问题。作为判例的裁判本身所具有的效力,比如基于正确性和正当性所产生的说服力、基于司法的独立性和终局性所产生的确定力、基于裁判者的人员构成和裁判的形成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力等等,不仅影响或决定着该案裁判是否会被后案引证为判例,而且一旦引为判例,将对后案的说服力、确定力和影响力产生直接影响。假如一个示范性判决错误可能导致批量错案;一个受到信访、再审等潜在威胁乃至撤销风险的终局判决成为判例,可能将一批后案判决置于不确定状态。因此,在裁判自身的权威性、确定性和终局性都普遍处于潜在挑战的风险之中的背景下,考虑裁判对于其他案件的效力,更需充分关注制度设计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否则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且蕴藏着新制度不可承载的负面效应和风险。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正在探索中的指导性司法判例,还是自主性案例选择,其价值与其说是形成某种制度性的拘束力,毋宁说是在于帮助法律共同体从案例中探寻裁判的理路,养成法律的思维;并在这个过程中,帮助社会共同体理解司法的特质,滋生法律的信仰。